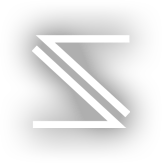2024年
1.3
看地震发生时NHK播报地震和海啸预警的视频竟然看得泪目,播音员在前面播地震情况时声音还尚平稳,后面接到海啸警报时声音一下紧急了起来,非常有感染力,到后面嗓子都能听出来有点嘶哑了
然后看评论说这是吸取了之前发布预警时播音员语气不够紧迫导致人员撤离不及时的教训,真是实打实地在改进啊。
另外就是,紧急播报除了日文以外还有包括中文以内的若干种语言轮流重复——这些把「人」放在第一位的考虑实在太让人感动了
1.6
补红白的时候不禁想到前一阵有人评论「文化入侵」时说「什么文化入侵,文化扶贫还差不多」
1.9
在读2008年出版的《中国:奇迹的黄昏》,看到这么一句:
「在中国,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有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他们的待遇甚至比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我觉得十几年过去还是有进步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只需说出「人矿」两个字就能互相心领神会get到上面那句话所表达的所有意思了,效率实在提高了许多
1.11
足球反贪纪录片最好笑的一句话是:「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权力过于集中」
不是因为它没道理,恰恰是因为它巨tm有道理但在大家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却无能为力好几十年之后,你装个大明白似的反而跟我们说这话
1.17
忘了之前有没有提过,在其他地方看聊起三年饥荒,我又想起张恺帆这个人:
他当时是安徽省副省长,在无为县调研时发现有问题,毅然决定开仓救灾、停办食堂,结果被猛批,遭到长期囚禁;亲友也被连坐批斗,或者送去劳改。后续在文革中继续被巡回批斗并受伤。
结果到1991年他去世的时候,遵照他的遗嘱并未举行悼念活动,却有上千名群众过了几十年仍自发去为他送行。
这拍成电影岂不是《窃听风暴》《辛德勒名单》的级别?
1.28
之前Clubhouse没被墙的时候有个五千人的房间聊六四,其中一位发言者说当时还是个小孩,只记得被他父亲带着去广场给学生送水(还是饮料来着?)。当时好多人轮流发言,不知怎的只有这件小事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结果过了两年,今天看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段,瞬间想起了当时听到的这件事,并且感动于还是有人记录的:
「北京市政府断了天安门广场的水以后,马上就出现了“学生没有水”的白旗。居民纷纷送水。各种可口可乐瓶、汽水瓶都装满了水,从四面八方送到广场。不少家庭的瓶子全收光了。北京市政府看到断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天就恢复了供水。但市民送水还持续了三四天。给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送食品、送稀饭的人更多。一位西安来的学生对我说:“我们不愁吃,不愁喝,全是北京市民送的。”」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1.31
在上海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完全不够了解这个国家,于是开始有针对性地读书,第一步是拆开了之前去香港旅游时带回家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并且接着一本本看了下去,感觉到现在算是稍微告一段落。
虽然我肯定依然总体上非常无知,但多少是建立了一些概念。
2.1
得有两三年没做过梦了,昨天毫无征兆地做了梦,竟然梦到的是和人聊了一路天……
说起来,我曾经做过的印象最深的一个梦,本质上也是在聊天(如图)
懂了,我的fetish是能开心聊天(

2.4
有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是,没有谁会为你避免了(又)有一个孩子出生在可能缺乏爱意甚至充满吵架的家庭这样的悲剧轮回而感谢你,相比于完全不在乎这些的人,你反而会格外地受到来自父母和各路亲戚的轮番奚落,且一年比一年猛烈。
就……这个社会的评判标准实在是太奇怪了。
说真的,就算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我都闪念过好几次要不他妈随便结一个算了,但真是每次一想到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一个人经历我所经历的童年,就又坚定了下去
PS. 不知之前有没有讲过,我的诞生可谓老中の目的性生育之典中典:我爷爷查出患癌,我爸火速结婚生孩子一点没耽误,成功让我爷爷「见到了隔辈人」。
我讨厌我这个诞生故事。
2.12
今天开心的事是在豆瓣上看见前女友老师拿到了京都某个学校的经济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附言是:
「这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不问利弊,不计得失,纯凭喜好做的大决定,仿佛是用过去十几年的努力换一次为期两年的任性。
终于有机会在鸭川边无所事事的虚度人生了。」
说实在的跟我同龄的朋友都肉眼可见地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日子人,看到她的这个选择实在太替她开心了,我自己近两年奄奄一息的心气儿也为之一振
2.28
「群星」这游戏我可能是DLC没买够,玩过几局之后觉得重复度很高,后面就再没打开过;但它的背景音乐质量实在是超高,后面我经常放它的原声专辑听。
所以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买音乐送了个游戏。
3.4
温家宝在2012年两会后的记者会上那番「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耳复失」的话语还言犹在耳,十二年之后,记者会这事先得而复失了。
两会总理记者会,1993 - 2023, RIP.
3.9
看到有在美国上高中的人发的留给他们的总统国情咨文观看作业,我不禁想起了前年那些组织学生观看()开幕式的画面,只不过我们的观看只是为了看()的仪式,而人家却是真正在培养学生关注国家政策的意识:
「你最希望总统讲述哪些议题?这些议题总统究竟讲得如何?」
「总统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总统最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是什么?」
「共和党的回应有哪些可取的地方?」
3.11
听「忽左忽右」聊前一阵去世的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利内,说起他曾经发起「智慧投票」(Smart Voting)运动,也就是由他的团队收集全国每个选区中最有可能击败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所推出的候选人的参选者,让人可以自行找到自己所在选区应该投谁以集中选票,最终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比如统一俄罗斯党在莫斯科丢掉了1/3的议席,甚至在2018年选输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行政首长。
这进一步引发了后续的蝴蝶效应: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由于该行政区不再配合当局做票,导致在2019年执政党在该地区一席未得,历史上首次完全失去对一个地区的控制。俄罗斯当局于是在2020年逮捕了这位民选的行政长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
就觉得,哪怕再有各种作弊手段,只要留着这种形式上的口子,碰上有足够耐心的人和足够多的反对者也能多少撕下其面纱,一窥其丑陋的嘴脸。
同时也感叹,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斗争方式啊,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3.28
Steam春促买了 #维多利亚3 ,感觉自己在疯狂为各个领域各个厂子指明方向:
1841年3月3日 为经济体制指明方向
1841年3月3日 为进出口路线指明方向
1841年3月4日 为杂谷农场的生产方式指明方向
1841年3月5日 为畜牧场的围栏样式指明方向
3.29
#维多利亚3 里面想改法律的话得看当前整个社会对这个议题的总体意见,这种表现形式算是形象地展现了什么是「观念的水位」对政策的影响。
另外一看到这些漠不关心的群体我就有端联想到国内现状😡

想起之前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里面记述了改开之初正是社会上自由派的声量和西单民主墙运动给了改革派助力,才十分艰难的突破了强大的保守派势力。这并不遥远也并不敏感的故事我竟然是自己找书看才得知的,改开的叙事被有意形塑成最上层几个人的人为设计。That’s not true. Our voice matters.
4.1
凌晨有个朋友惊呼才意识到 #HIMYM# 已经完结整整十年了

4.15
看采访milet的纪录片,里面提到她作曲的方法是「脑补一些影像片段,然后给这些片段加BGM」,我看到这脑内虚拟地拍了下大腿——这解释了她的「Hey Song」那支MV为何歌曲与画面的节奏和走向如此搭。我之前看的时候就想,这个MV简直太适合用来照着模仿每个分镜,给伴侣拍旅行Vlog了,原来一切其实都有迹可循

4.20
I’m pretty sure that last year was 2022, and the year before that was 2020.
4.21
前两天在大银幕上重看《暖暖内含光》 ,意识到自己最喜欢的两句影视剧台词都是单拎出来没啥意义的短句——
一个是这部电影里男女主角逃离记忆清除到走投无路时,「这是最后的记忆了,我们怎么办?」「Enjoy it.」
另一个是之前说过的<HIMYM>第九季,「你在干什么?」「Remembering this.」
4.27
实在是太久没出门了,这两天看电影才发现小区到地铁站沿途唯一的一家便利店关张了,积水潭站到电影资料馆沿路唯一的一家便利蜂也是。
以下可能有点过度展开,但想想曾经抱怨北京便利店不够多的那个自己大概已经算是幸福的了,「不够多」还蕴含着「能有更多」的可能,而这种「一切都会变好、只差时间」的信心正逐渐被摧毁中
5.3
前两天借着最近的小津观影浪潮又重新看了遍《东京物语》 ,2017年时自己不情不愿地往高打了个四星,写短评说是个「匠气、工板、刻意的寓言」,现在则完全认定它确实是五星作品。其差异有一部分来源于后面又看了许多其他作品后对当年表演方式的适应,更主要的是更加理解了人生「想做」和「能做」之间的鸿沟。片尾小女儿说「我不想变成他们那样」,这也许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初心,但能一直保持下去是件超难的事情。这件事可以是片中1953年原节子角色的「孝顺/尊重老人」,也可以是任何年代的任何其他事情
5.11
晚上跳着重看了下《大话西游》,感觉如果真想认真审视里面「爱情」主题的话,这片充其量只讨论了「爱情」的表象。
这片男女主间的关系,始于「拔出剑的就是我的意中人」的无厘头设定,然后一个宇宙级的美丽女子就开始犯花痴,两人之间似乎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可供支撑「爱情」的化学反应,换句话说就是「男性意淫中的爱情」。上个时代的人认知中的「爱情」也许是这样的,因此没感到违和,甚至会为之感动;可现在已经不行了——至少我希望是,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写出《倾耳倾听》《花束般的恋爱》这样细腻好本子的土壤。
很有趣,片中还有一句针对这种质疑的反问「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我看最好需要一点,当然这些理由不要是那些「相亲硬指标」就行
5.30
偶然发现陈强和陈佩斯父子在豆瓣影人的形象是颠倒过来的,父亲反倒比儿子年轻了

6.8
偶然看到文明6里面引用了一句简·奥斯汀的话:「在我所有重要的毫无意义的事里面,我应该先告诉你哪一件呢?」
查了下出处,是来自她写给家人的一封信的开头”Where shall I begin? Which of all my important nothings shall I tell you first?”这个”important nothings”的表达真是又可爱又精妙啊。
而且随着现代社会不断解放的个人主义,这种「对自己重要、对别人毫无意义」的事会越来越多,Jane真是领先时代200年。
6.13
这几天很偶然地先后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和《末路狂花》 ,这俩电影也太对仗了,分别是描绘女性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的东西方版本,结局也完全彰显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甚至观众也是:觉得《末路狂花》 极端的建议去看前者,那里有你想看的隐忍;觉得《大红灯笼高高挂》 平淡的则可以移步去看后者,希望你不要眼珠一转又觉得主角极端了哦
7.19
最近搞对外免签,听说紧急处理了外国人住店时只许在指定的有资质的酒店入住并报备的问题(90年代何伟在中国自驾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事)。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下弄不好一个外国人在内地住宿时要比维族人入住还方便了,这也太地狱了……
8.27
话说前几天想溯源一下网证这玩意的政策来源,从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目中三搜两搜,偶然间搜出个熟悉的名字来 :0010:
无论怎么看,这玩意都差不多是2018年就开始酝酿立项了,到现在砸了不知多少钱完全跑通了才出来「征求意见」补一下合法性,明摆着就是没有任何诚意的

8.28
前一阵知道个可以在线翻历史任意一天人民日报的网站,出于好奇翻了不少。因为我觉得,比起之前看专著、讲座或者维基页面,这些报纸上的东西(虽然完全是宣传工具)反而更接近于当年的普通人所能接触到的视角。
翻阅时的想法自然有很多啦,暂且不谈细节,先说一个很总体的感想,就是我怀疑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很普遍的「二极管」思维,也许相当程度上受到几十年来官方叙事的形塑:在报纸上你很难看到对一件事或一个人全面、客观的评价,相反前两天还无限伟光正的大人物突然间就被「批倒批臭」扣上无数帽子的情况比比皆是。我还注意到这种批判不光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号上,还会煞有其事地刊登出一些「事迹」来坐实其罪恶昭昭,但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许多「罪证」都看起来像编的。
讲道理,还有句当时被高频引用的毛语录也是典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凭什么啊?
也许就是在这样极其缺乏多元视角的社会氛围中,潜移默化地让身处其中的人也用同样的逻辑去审视这个世界了,并且贻害至今
9.7
前一阵看电影《妇女参政论》(<Suffragette>)时被一句台词打动了:
You want me to respect the law, then make the law respectable.
然后搜了下发现这句话有原型,来自1930年代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民权律师Louis Brandeis:
If we desire respect for the law, we must first make the law respectable.
相比之下,我们的「法官」别说说点这种人本主义的话了,反而满口「对错误思想亮剑」
9.17
昨天听播客里面讲日本的「夫妇别姓」议题,这个对我们来说毫无问题的现状,对日本的许多保守派来说却难以接受,而且反驳的角度超出我的想象力「孩子要是看到父母的姓氏不一样会不会产生迷惑?这怎么能算是一家?」但其实本质上却是他们缺乏想象能力,因为这与他们从小的传统不一致。这件事与楼主讲的很相似,一件完全合理的诉求,仅仅因为「与惯例不符」,就遭遇无数人本能的反对,哪怕本身就是受害者都很难从这个庞大的体系跳出来
9.17
十几年如一日靠着寻找各种治愈的东西维生,忘了之前有没有感叹过机核安姐的声音就有种治愈的力量,这条评论说得太好了,维生素Ann!

10.5
在一个dc群里引述了之前自己留意记录的一段刚翻出来的人的心态(「翻出来看到墙外大多数内容的文字是英文或者是繁体中文,就觉得自己“到了一个自己不该到的地方”」),竟然引来了李如一老师有感发了一篇blog《去不該去的地方》。
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连结的可能性真的太奇妙了。
(如果你具备翻越技能的话
11.13
所有能进行回复的网站/app都应该加个静默回复的可选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回复别人并不是真的想和当前的这个特定的ID进行一番争论(经验表明这种争论大多没有意义、徒增烦恼),只是想让后面到评论区的人看到原来还是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补充一些基本的fact-check,这时就完全不想、也没必要让对方收到评论通知
11.21
昨天香港47人案判决,听世界苦茶的节目里面主播哽咽的声音,心情也很差。
这些人被判四到六年,理由仅仅是他们试图运用民主框架内的程序来瘫痪议会——在美国,政府停摆是个隔几年就会听到的见怪不怪的新闻,也没见卡预算案的议员被抓起来;而在这里,它却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BBC中文那边虽然高赞也是在声讨的评论,但按最新留言查看就能看到大批冷嘲热讽。这让我想起不朽的《茶馆》里的一幕:庞太监说「消息下来了,谭嗣同问斩」的时候,旁边有一桌的一个人偷偷问:「谭嗣同是谁啊?」时隔这么多年仍然很符合这些冷漠的人的形象,不去了解,觉得与自己无关,甚至被朝廷的布告先入为主觉得他们不好……